面灯
■ 郑天华
古往今来,城里和乡下就是有区别的,这也包括了元宵节的灯。城里的灯豪华显耀,适宜街张巷挂;乡下的灯质朴平实,方便杆挑手提。但就承载的文化内涵来说,乡下的灯绝不比城里的灯逊色。在又浓又酽的乡情乡韵流淌成的那条漂满民俗的岁月之河里,汹涌澎湃的潮头远远高过了城里。
在山东茌平,元宵节的灯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堂屋门旁,竖根杉篙,顶上拴上芝麻秆,挂满松枝,固定好滑轮或铁丝圈儿,用绳将吊好的灯拉上去,这叫天灯。把收集的马蜂窝用油泡透,串在一起,固定在底部留口的球形大纸壳里。用热气球的原理将马蜂窝点燃,靠浓浓的油烟和热气,将透着光亮的纸壳拱上天空,随风飘游,这叫云灯……
天灯好看,云灯好玩,但不是家家都有。家家都有而样式各异、每户又都不止一盏的,是面灯。
面灯传承了多少年,已无从查考。人们只知道:奶奶的奶奶,元宵节就做面灯、点面灯了。像“腊月二十三,灶王爷爷上西天”,要“离岗述职”一样,正月十五元宵节是民俗中“灯姑奶奶”回娘家的日子。这一天,忙了一年的油灯被擦洗干净,用红纸包好放上供桌,担当照明任务的便是面灯了。
农家的女人吃罢午饭,就早早和面做面灯。她们做出的面灯各式各样。最简单的是捏成圆形的平底碗状;复杂一点的做得像画家的调色盘,中间一个稍大的,周围一圈儿小的,呈众星捧月之势;还有的做成一座灯塔,层层叠叠,煞是好看。至于那些活灵活现的十二生肖面灯,就应该算作民间艺术绝活了。
天一擦黑,各家各户的面灯次第亮起。堂屋的八仙桌上,厨房的灶王板上,门枕上、窗台上、床头上、炕沿上……到处都摆着面灯。用弹过的棉絮搓成的灯捻,吸饱了弥漫着香气的菜油、棉油,柔美的光照得屋里一派通亮。
家乡还有小孩看一个灯头长一个心眼的说法,所以各家的面灯点亮后,大人便催促孩子到四邻八家去“看灯”。小孩都是“炕头上的光棍”(当地方言,只敢在家门口逞英雄的意思),有的只是群胆。一个人去看时还探头探脑,三两人结伴便有点胆大气壮。待到几家的孩子凑成一团,便欢呼雀跃起来,每进一户家门,就乱喊乱叫:“看灯了!”“看灯了!”后面的还没挤进去,前头的已往外挤了。这样挨门挨户地串,看遍大半个庄子。
待把自己的孩子撵出去看灯,打发了看灯的小客人们以后,大人们还有一个活儿:照厅。所谓照厅,就是把面灯放在盘里,一手托着盘,一手遮着风,将屋里的墙角、门后、桌底、床下、旮旮旯旯,统统照上一遍,让平时灯光照不到的地方都见到光亮。院子的边边角角,甚至牛棚、猪圈、狗窝、猫洞、厕所……也要照个遍。边照边念念有词,做着祷告、许着心愿、呼唤着神灵、震慑着鬼邪……因为民间传说中,一切鬼怪妖邪,都是怕光亮的。所以照厅的意义,就是保障一家不受鬼邪侵扰。
吃灯是每年正月十六早晨的一道美味。灯的吃法,各家都有不同,每年变着花样。最常见的是加上葱花、肉丁、五香面,烙成油饼或蒸成花卷。至于十二生肖灯,为保持其外形,吃出情趣,就原样上锅蒸了。一般做面灯时,就按全家每人的属相各做一个,吃时自然也按自己的属相吃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吃着面灯,期盼五谷丰登,家庭幸福,生命长存,农家将中华食文化丰富到了极致,形成了一首意味深长的田园诗。
流逝的岁月,使无数令人陶醉的乡间风情成为遥远的记忆,但朦胧中,家乡的面灯仍是那么温柔,那么和谐,那么明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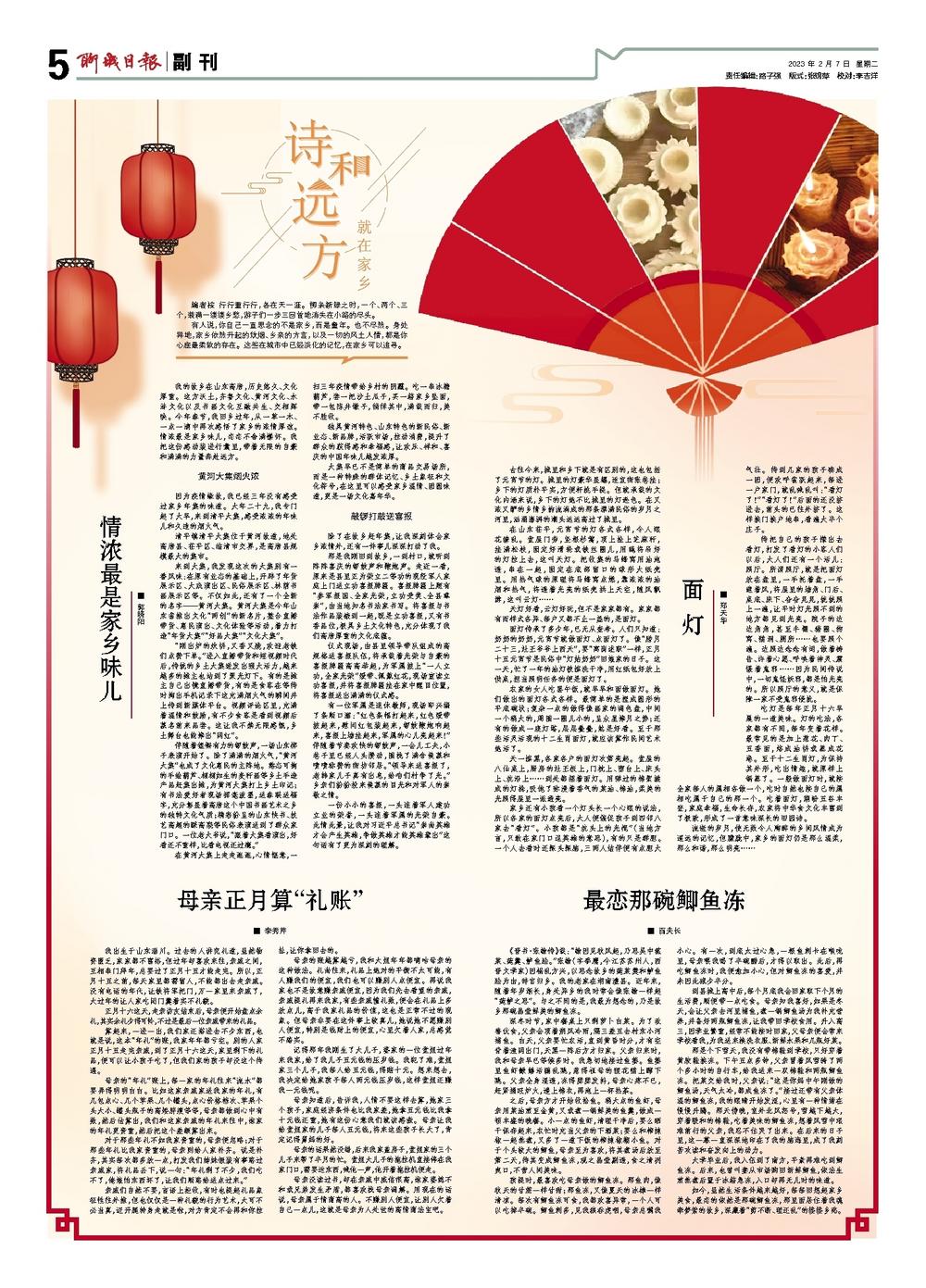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