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的饼,壮壮的馍
■ 赵勇豪
馍、饼之谓皆因面起。
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土肥水沃,是优质冬小麦的主产区,聊城的饼、馍原料充足,加之聊城系齐鲁、中原、燕赵、秦晋多元文化的碰撞融衍地,饼、馍的形式丰富多样自是不难理解。
制具极简的吊炉烧饼从广袤的中原大地河南、安徽一路向北,过黄河式微,形也剧变。“黄河聊城”(也就是聊城的南部)尚是正宗的吊炉烘烤烧饼,所谓吊炉系铁锅倒扣,外涂黄泥和马鬃保温,内烤木炭火,形制粗犷,简单实用。聊城城区小街巷口虽然布满了烧饼摊儿,但已经出现了不少转动式铁板烘烤烧饼。据我实地访问,铁板烤多是受冀地影响较大的冠县商户。若去东昌府的乡镇,大油火烧多见,一种面团里揉进葱花油盐的长条形饼在铁板炉上先烙后烤,让人联想到东昌府的呱嗒。我想强调的重点是,火烧的称谓出现了,炉具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再往北,临清、高唐则再无吊炉烧饼的踪影,火烧面孔几变,三角的、圆形的、方形的,动不动还夹了昂贵的牛肉、驴肉。
比之吊炉烧饼北上易容和身段变换的艰难,向南走则亲切多了。一路过黄河,铺开菏泽、濮阳,直上中原的腹地,传统吊炉妥妥的,焦黄的烧饼舌头,轻易可以望见烧饼师傅的不惜力气和用心。至于芝麻的多寡,我始终认为那不是吊炉烧饼的重点,虽然辽阔的中原地区是现代中国本土芝麻的重要产地。
窃以为,聊城吊炉烧饼首推老寿张县城吴家街吴家烧饼。
肉饼虽也属饼类,但它们距离面食的主食有些远了,况且,在农耕文明的腹地,薄面皮里塞满鼓囊囊的肉馅儿,对于老百姓来说实在过于豪奢了,馅儿的内容和意义远超了面皮,滑向另外一个品类了。
黄河的豪迈和宏大投射在黄河岸边人民的生活日常里,大锅饼和壮馍最是不容忽视。聊城境内有东阿牛角店韩寨锅饼和高集锅饼、阳谷张秋壮馍,友邻河南濮阳也有壮馍。东阿的锅饼、阳谷的壮馍都是纯面的,濮阳壮馍是肉的(饼),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形制巨大,动辄几斤面几斤肉馅儿反复滚揉成一个和锅同样尺寸的巨无霸,那里面得隐秘着多少黄河人民关于生产组织的思想和生活里的不羁无拘啊。
同样是巨无霸,临清武德奎肉饼和濮阳的壮馍差不多,都是薄面厚馅儿,明油煎烙,形式和烹制基本相同,但细考量,黄河农耕文明和运河商业文明的养成还是有差别的。濮阳壮馍以大葱、粉皮和以肉馅儿,葱成段片、粉皮撕条、肉切片块,材料形状极力呼应着名谓和主题。而临清武德奎肉饼以京瓜、葱丝、黄姜、板油、甜酱和以肉馅儿,微丁近泥,浑然一体,魁伟粗犷里透着商埠的细腻。尤其是京瓜的加入,使主辅料的合理搭配在穷苦或富足时都极有道理,左右都是关怀体贴,这应该是商业文化遗落的精明和智慧吧。
在濮阳壮馍和临清肉饼面前,阳谷肉饸和莘县康园肉饼可谓小弟弟,但小弟也有个性,招式里挥洒着黄河豪放的大写意。你看,阳谷肉饸起身于乡镇集市,最后攻城掠地于县市,从圆形到矩形,形制几度扭曲,从粉条素馅儿到牛羊猪肉的满馅儿,从小巧单薄到臃肿富油,一路风雨沧桑,但浓重的花椒面一直不敢省,油香肉香是为张扬的麻香铺垫,大快朵颐,让人过嘴不忘。那份殊烈的麻就是阳谷肉饸的灵魂,骨子里的硬气让人不敢小觑。莘县康园肉饼的炉灶上,烙饼师傅手持两把比脸都大的大刀,反正上下,也铲也切,活儿是倍儿利索,心性和美味也是养得敦实厚重。
这两样食馔在辅料上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粉条,盖因粉条系本地常见好物,红薯收罢,秋耕秋种忙完,闲下来的劳动人民正好捞粉条、晒粉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粉条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产物,漫长的冬日,一锅白菜炖粉条足矣。
吊炉烧饼、大小肉饼、高桩馍馍、大壮馍……饼饼馍馍,大大壮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硬气。这是黄河的硬气,更是黄河岸边劳动人民的硬气。广大劳动人民与大自然与困难艰苦斗争养出来的硬气,很黄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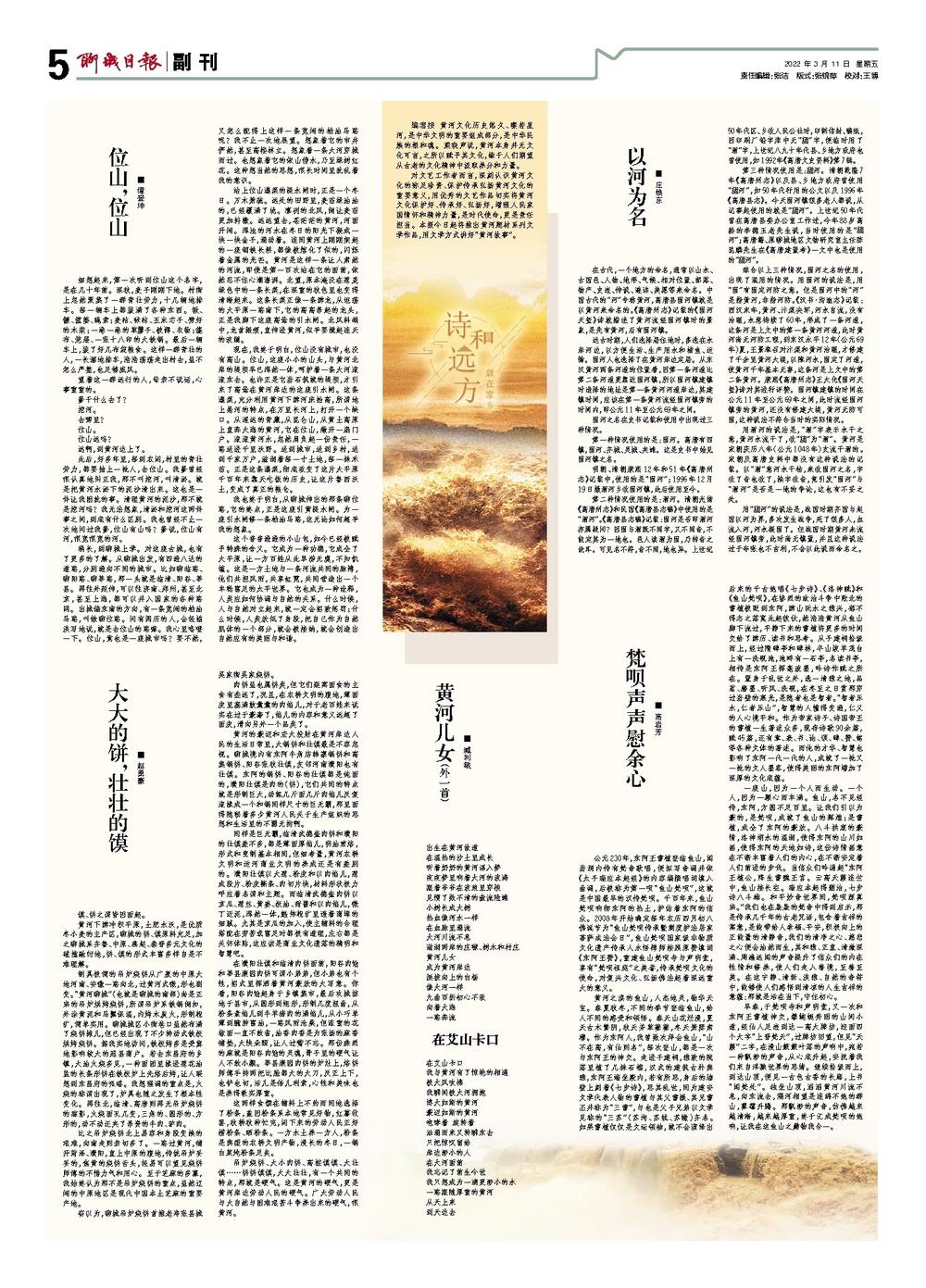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
鲁公网安备37150202000134号